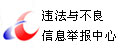这些年,谁伴我长大
当下,留守儿童的成长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。记者历时半年,前往河北、河南、浙江等地,走访了十几名留守在家的孩子、在外打工的父母,以及长期关注留守儿童的社会工作者。走访中发现,留守儿童在心灵关爱方面存在缺失,与父母之间缺乏有效的情感互动。
“除了钱你还给过我什么!”想起女儿在电话里的质疑,在外打工的妈妈失声痛哭。
常年在外,很多父母疏于沟通,爸爸妈妈成了“打钱的人”。采访中,我问过多个孩子,当你遇到困难、烦心事,会给爸爸妈妈打电话说吗?孩子们大都回答:不会。
低年级的孩子会说:他们听不懂。小学高年级的孩子说:如果说了,父母会担心、牵挂,认为自己不开心。再大一点,进入了青春期的孩子们直接回答:不想说。
农村里,环境封闭,少有外界信息输入;看护孩子的老人们大多文化有限,体力不支,常常一对老人带着几个孩子,教育上力不从心;学校则受制于师资、经费,资源相对比较匮乏。如果没人爱,孩子就野了,这成为很多乡村老师的担心。
在家的孩子:
爸爸说,考不好我揍你
“你好好学听到没,考不好我揍你。”之前的一次通话,爸爸告诉王婷婷。
北冶小学期中表彰大会,王婷婷得了六年级第二名,比第一差了0.5分。拿着奖状,她微抿着嘴,脸微微泛红。
“你考得不好就该不告诉我了。”王婷婷估计,如果打电话告诉妈妈成绩,她一定会这样说。
校门外是绵延的太行山,北冶小学在河北平山县北冶乡,一所寄宿制学校,上10天,休4天。开完表彰会就放假了,爷爷来接婷婷。她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,爸爸在陕西,妈妈在石家庄。家里有妹妹,还有一条跛脚狗为伴。
平时,爸爸的联系不多,妈妈电话勤一些,每次都问学习、天气、饮食,有时问题重复,婷婷就烦了。
快到晚饭,婷婷去接妹妹。看见婷婷,6岁的妹妹老远就冲过来一把搂住大腿,上蹿下跳,婷婷则板着小脸。平时放假,婷婷会拿着作业去幼儿园,边写作业边教妹妹拼音。幼儿园20多个孩子,只有一位60多岁的老师。婷婷对妹妹很严厉,因为“我妈就是这么对我的,我想让她也好好学习。”
回到家,饭已经好了,老人身体都不太好,年初,爷爷病了一场,“花去人家一年打工挣的钱。”爷爷叹气,“必须在外面赚钱啊,过年才能回来。”家里没什么合影,只有两张,还都是婷婷很小的时候。
吃过饭,妈妈来了电话,“你的语气不坚定,一定考得还不够好。”听了婷婷的成绩,妈妈这样说。婷婷没有争辩,一副“就知道会这样”的表情。
和婷婷一样,北冶中学的李苗听爸爸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“你得好好学啊!”
爸爸在石家庄,李苗和弟弟跟着多病的妈妈生活。放假时,李苗先写作业,然后做家务、卖破烂。干活时,她会想以前,跟着爸爸出去能问东问西。现在,爸爸的电话很少,回到家话也不多。偶尔,李苗会问,石家庄什么样啊?爸爸看着电视说,就那样吧。
李苗想爸爸回来,但又怕他回来喝酒,怕他喝醉了发火,跟妈妈吵架。她想,如果成绩好,爸爸就会高兴,不那么辛苦了。李苗很爱学习,也很着急,最近历史地理考得不好,一些老师没强调的知识点,她就忽视了,结果丢了分。晚九点,宿舍熄灯了,李苗还趴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课本,现在,除了看课本、做题,她已经没有时间看别的了。
出来的父亲:
不怎么跟孩子聊天
掏出手机,石彪按断了姐姐的视频请求,他刚从北京的呼家楼上了地铁,至少一小时才能到达天通苑。晚8点,地铁晚高峰快过了,但依然没座。农村的夜静,估计姐姐和儿子马上就要睡了。
过年回来,石彪一个电话都没给家里打。他在北京做理财销售,一个项目赔了,他以为是暂时的,先掏钱垫给了客户,结果真出事了,30万没了着落。30万,这在农村就是一个天文数字,想到这他就噌噌地冒火,也不愿和家人联系。只有姐姐,时不时跟他微信联系着。
6岁的儿子留在老家,爷爷奶奶带着,姐姐在时他偶尔跟儿子视频,每次都问吃什么了?学什么了?没两句,儿子就烦了,跑去看电视。
“你跟儿子的感情深吗?”听了我的提问,石彪愣住了,沉默了一会,他说“不太深。”
很早,石彪就来北京打工,即使有了孩子,每年在家的日子也屈指可数。
石彪喜欢城里,他说这里充满可能,而家里的日子一成不变,年轻人根本呆不住。即使过年在家,大多时间他也在看手机。
刚到北京时,因为只有初中文化,石彪只能在家具厂打工,他不甘心。后来,机缘巧合,他做起了理财销售,觉得这职业太好了,“能接触到很多成功的人,很高端,跟他们聊天都在成长。”
到家已经很晚了,天通苑的屋子是与人合租的,一个小单间挤着两张床。躺在床上,石彪继续工作,不停地发微信、打电话。他说做这行就要常沟通,没事也得联系着,维护感情。
“那你会经常跟孩子聊天,讲你在北京的见闻吗?”我问,“不会,说了他也不懂”,想了想,他又说“也不是,其实,他能听懂。”
这半年石彪和在广西打工的老婆也毫无联系。“关系不太好,想法不一样了。”但他没什么时间想这些,每晚,他都会发一条朋友圈,内容多是梦想、挫折、奋斗。最近两天,他发了“人生的路都是逼出来的”“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”。
有时,他会想儿子,想起上次走时儿子已经睡了,没有告别,第二天醒来后儿子有点难过,说早知道爸爸会走我就不睡了。可他觉得没办法,“我得赚钱啊!必须要赚很多钱,才能买房、买车,给孩子更好的教育。”
“那你觉得什么是更好的教育?你希望孩子能成为什么样的人?”
我的这条微信,石彪没有再回。
长大的留守儿童:
不想再让孩子像我一样
前些天晚自习,班上一位男同学玩游戏,曾燕批评了两句,学生直接顶撞她:我爸妈都不管我,你管我!曾燕很生气,也有点心酸。
她在杭州的一所艺术学校教语文。没人管,这是曾燕记忆里的常态,也是如今仍在老家的表弟表妹们的现状。
上世纪90年代初,曾燕还在重庆上小学,父母受亲戚的召唤去了广东打工,然后,每次回来他们都会带走村里更多的人,几乎全村孩子都成了留守儿童。
“房梁泛着黑色,一根布满灰尘的电线,一颗昏黄的电灯”,这是曾燕记忆中年底的团圆,没有温馨话语,甚至有点别扭,她和弟弟拆完礼物,问完期末考试的成绩,全家无话可谈,于是睡觉。
她已记不清当时是否有思念父母,觉得习惯了,就该那样。
现在,三叔、小叔的孩子们还都“留守”着,不同的是,农村的老家基本荒了,孩子们住进了镇上的楼房。小叔家是姐弟俩,他们各管各的,彼此很少说话。即使小叔在家,也是一天都在外面钓鱼,很少管他们。过年团圆,爸妈会像大款一样带他们去买东西,孩子们很高兴,但爸妈离开时,他们似乎也很平静。
一次,小婶子初六就走了,出门发现忘带东西又折回来,她偷着问小叔“他们哭没有?” 小叔笑着说:“哭什么?他们知道你要走的,有什么好哭的?”
曾燕的庆幸在于,当时学校还抓得很紧,自己又遇到了非常负责的老师。考上大学那年,妈妈专门坐飞机回来送她,感到无上荣光。不过,许多年后,当她30多岁还没结婚,妈妈似乎又很没面子。她的同学们大多十七八岁就结婚,有的已经结了又离,离了又结。她们中的许多人生完孩子又扔在了老家,重复着自己的过去。
“人最可悲的是在本该奋斗的年纪却安逸而不自知。”这是曾燕现在最大的感慨。她觉得自己能上大学是侥幸,当时浪费了太多时间,后来遇到那些“学霸”同学后,她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求知。现在,对于婚姻、生育,她十分审慎,希望将来孩子不要像自己一样。